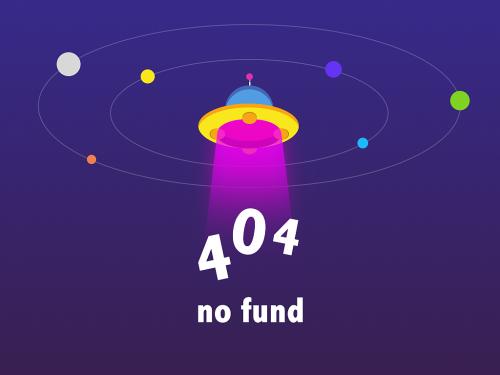平和走过人生-37000dcm威尼斯
作者:丁清 供稿单位: 发布时间:2014-05-05 浏览次数:
正如白岩松说自己做主持人最难忘的一段日子,是在采访季羡林等11位学者时。因为这些学者们“带着一生的坎坷,非常平静地面对你,每一句平平淡淡的话后面都有特别耐人寻味的东西”。很有意思的是,在采访陈彭老师的过程中,他那始终平和的语气和声调,也让我有了这样的感触。当可以平和地回首人生走过的或平坦或崎岖的路,并用那么平静的语言叙述时,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去面对了。
陈彭是1932年出生,当他在1987年,从机械系主任的岗位升任副院长时就已55岁了,3年后他升任为院长。1993年突发脑血栓离职,1995年退休。
读到这样一份特殊的履历,多少有些让人吃惊。
那么,在副院长和院长岗位上的六年时间里,浑身洋溢着知识分子气息的陈彭,究竟做了哪些值得在学校发展史上记录的功绩?在短暂的六年时间里,他完成了什么心愿,做出了什么改变呢?又是如何践行了一位高校领导的职责呢?
带着这些疑问,2014年的一个冬日,我走进陈彭老师的家,坐在茶几旁的一张小椅子上,打开夹子。他慢慢地走来,小心翼翼地在沙发上坐下,夫人张瑞瑜拿了条薄薄的小被子盖在他膝盖上。想起我只有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我忙把手表褪下,放在边上……尽管是上午,持续的雾霾却使客厅的光线依然很昏暗。陈彭老师便说:“打开小台灯吧。”灯泡坏了,光源方向也不对,最后还是张老师拿来书房的台灯。
我心疼地看看时间,已经“荒废”了5分钟。
重新安静地坐下。我很好奇地询问:“您与桐城派之间,有没有渊源啊?”陈彭马上很肯定地作答:“一点没有。”但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地域和血脉里揉进的遗传基因,是一定会在生命里体现出的。
我清楚地记得读书时,一位学识渊博、备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在分析作家和文人的人物性格时曾提到:鲁迅因为小时候整天去当铺和药店遭白眼,目睹了世人的真面目,故其作品中有穷尽一生的呐喊,造就了其性格的深沉和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而郭沫若则不同,少时生活在山清水秀的四川乡间,衣食无忧,便无法不带着家乡的灵秀,创作出《女神》、《星空》、《天上的市街》等浪漫主义作品。
因此,清朝中叶著名散文流派“桐城派”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主张文章思想放在首位,艺术则相对独立。这些,无疑是因为地域和民风的浸润。陈彭或许因受桐城派流风影响的缘故,身上那种无法遮掩的学者的率真和直爽,更显得真实和亲切,作为主管财务、设备和图书馆的副院长,他敏锐地发现了学校财务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审核不严格,签字制度有些混乱,这已给学校造成了不小的损失,损害了学校的声誉,有关领导在全院大会上几次专门谈到这类问题。为此,陈彭很坚决地提出加强财务监督与管理的建议,并由此建立了一整套详尽的财务管理制度。
追溯到最初参与筹备创建机械工程系时,他的思路就明确地立足于开创电力机械动态特性研究专业方向。在相继创建了机械动态测试与分析实验室及研究室、建立了硕士点和学术梯队后,在他担任发电厂工程和机械学专业研究生导师时,开设了机械动态测试、随机振动与谱分析、机械故障诊断学等多门新型专业课程。在担任院领导后,他的视野落在了专业技术的发展上。
为深入研究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扭振响应模拟实验,他曾专程和王加璇院长一起,找到电力部领导,申请了30万元经费,主持开展了振动、冲击、噪声等重点学科的科研研究。其中,“大连第三发电厂噪声治理方法研究”,获劳动人事部1988年劳动保护科技进步四等奖、“恶性事故预报———裂纹转子特性研究”获能源部1990科技进步二等奖、“东方300mw汽轮发电机组轴系扭振响应模拟实验研究”获电力部1996年科技进步三等奖。
升任院长后,他大力支持火电厂仿真技术科研项目的推广与应用。我校在国内率先设计制造了一套 “火电机组全过程仿真”系统,用仿真模拟系统取代锅炉、汽轮机等热力系统设备,取代发电机、励磁机等发电系统设备。系统可模拟火电机组开机、停机、故障处理、并网发电、电网换型以及发电机无限大系统等,对电厂和电网运行人员的培训实习,有着很好的应用前景。
陈彭从前期开始支持王兵树等人搞筹划设计、测试和安装大型火电厂仿真模拟系统,到后来邀请电力部领导到学校来参观,最终拍板由电力部生产司出面,邀请媒体出面,在宁夏现场召开“火电机组全过程仿真”系统设备鉴定会,使学校的火电厂仿真技术得以推广与应用,在国内电力系统赢得了声誉。1992年,该系统获得了当年的国家“十大科技成就奖”。
在学校发展面临瓶颈时,他与院领导班子讨论决定,扩大学校规模。这个决断,顺应了学校发展的需要,也得到了电力部的大力支持。为了扩大学校建设的影响力,他还专门去部里请相关领导来二校区出席开工典礼。
其实,与需要绕行一条日渐拥堵的小道才能抵达的二校区相比,当时有一大片与学校东西毗邻的农田更适合学校征用建设新校区,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没能把握住机会,形成东西两院的便利格局,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走回陈彭老师脚下的路,让我们看看他一生走过的是怎样的历程?
陈彭三四岁时,就随做银行经理的父亲来到上海。父亲的收入使全家人可以拥有优越的生活。他的小学是在教会学校进德中学附小读的,中学是在光华大学附中读的,大学考入杭州之江大学,后并入浙江大学。
他至今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每天要经过一个加油站,那里有日本兵站岗,每次路过时都要躲着走。从安庆到芜湖时,他们的船刚刚从码头离开,那码头就被日本人炸得一片狼藉。
在之江大学读书时,大一大二是不分专业的。学校不少教师都是外国人,所以英语教学水平不错,这些老师直到抗美援朝时才离开。读书时的陈彭各科成绩都不错,英语免修,但他不太喜欢化学,后来选择的专业是当时国家急需的机械专业。当年的机械分为制造和动力两大专业,动力主要研究汽车发动机。
1953年他从浙大毕业后,先是分配到沈阳。从上海坐火车出发,途中遇上发大水,在天津等了两周,才终于到了沈阳。作为小组长的他,很单纯义气。负责分配的人告诉他,一些学生不愿意去哈尔滨,说那里太远太冷了。他一听,马上就表态,“那我去吧!”
这个从小在大上海长大的年轻人,被再次分配到了哈尔滨航空工业学校。来读航校的学生,不少是从部队转业的军人,他们把这个年轻的老师当作了小弟弟,时常会很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刚21岁的他,在这样温暖的环境中,精神和身心都非常快乐。
那时的教课要求从开场白,到每一节的中心、重点和总结的流程,都要控制在课时内完成,苏联专家还要求他们全部脱稿授课。所以,他常关起门来,一次次看着表试讲。而且,作为教师,在穿着打扮上,苏联专家也是手把手地教他们。没有干净整洁的衣服,试讲没有通过,都不能登上讲台。
北国的天气,很快就结冰了。从南国潮润的葱绿中,来到冰天雪地的世界,第一次看到漫天飞舞的大雪,感受着童话世界里奇特的寒冷,让年轻的陈彭兴奋极了。他们热血沸腾地来到松花江岸,从江边高高的木质滑梯上,飞速冲进江里,四仰八叉地滑落在冰面上的滋味,真的很刺激。
周末和假期时,不少年轻人在江畔举办舞会。陈彭还记忆犹新当年发生的一次历险。一次,他在江边很开心地又吃又玩,还没过瘾呢就半夜12点了,这时有轨电车早停了。从江边到航校宿舍,要经过一片森林,而且森林有好几个出口。当时,他在漆黑的森林里不停地走,脚下踩着一地落叶,一步步甚至都能听到心脏的跳动。也不知道森林里有没有“黑瞎子”?还好,转了半天,终于顺利地走出了森林。年轻多好,能这样“疯狂”一把,至少可以证明生命是如此多彩。
那时,家里怕他在北方生活清苦,不时地给他寄钱、寄东西,加上自己也挣钱了,就经常去划船或坐小汽艇兜风,玩得很潇洒。
航空学校的文化生活很丰富。张瑞瑜老师在南京航空学院学的是飞机专业,可人很活跃,经常出现在学校的话剧舞台上。有次,陈彭看了张瑞瑜演出的话剧后,“年轻的心里有了些懵懂的想法”。恰好有位比张瑞瑜高一届的同是南航校友的军人,来帮他牵线。经介绍两人相识后,陈彭趁热打铁,热情地请张瑞瑜看电影、游江畔……张瑞瑜老师直到现在看上去依然端庄、丰润。张瑞瑜出身京城名医家庭,父亲在协和医院工作,解放初期创建了北大附属医院口腔专科。两人相似的优裕家境,相同的良好教育,使得他们一生琴瑟和谐。陈彭很幸运,那位当年让他砰然心动并一眼就看上的姑娘,成为他这一生相依的伴侣,而且在一起“坐着摇椅慢慢变老”后,依旧将彼此视为“手心里的宝”。
大跃进后的1959年,航校的老师们和整个国家一样,也被饥饿折磨着。学校里教化学的一位老师一次在食堂吃饭时,发现碗底竟然沾了张一两粮票,高兴极了。那时谁要是丢了一两粮票,回家后肯定会大吵一通的。不过,即便在生活如此困难的阶段,学校的教学工作还是很认真的。
文革中,陈彭夫妇没有躲过厄运。他被派去烧锅炉,夜里就睡在锅炉房里搭的板子上。我马上问:“那不是要吵死、脏死了?”他接着说了句:“还热死了呢!”两个孩子那时都还小,老二才一岁多。不久,全家人又被赶到安达农村。好在出身名医家庭的张瑞瑜,能够放下身段,在院子里种菜,养鸡。陈彭尽管力气不大,可也学会了打草。他比划着,在长长的棍子头上固定着镰刀,需要挥动臂膀去打草。
村里安排两家老师住一户。他们和一位姓叶的老师共用一间灶房,一起住了三四年后,终于熬到落实政策了,学校因属军工专业划归哈工大。夫妇俩在学校被整得有些伤了心,就申请调离回南方工作。也是凑巧,我院人事处处长李玉明去要人,正好缺搞机械专业的。看到了陈彭老师夫妇的资料后,当即拍板。就这样,陈彭夫妇高高兴兴地走进了河北电力学院,接受了参与创建机械系的任务。用陈彭的话说:“这里还有了个小插曲”。
当年,关存和老师带领他们一帮人,去上海江南造船厂参观考察和收集资料。可没想到一去就碰了钉子。上海江南造船厂是军工企业,联系考察时,人家根本不接待。好在陈彭曾经工作的哈尔滨风华机械厂属于航空企业,原归三机部后转归六机部。那时他因工作需要,与归六机部的军工单位造船厂打过交道。于是,他凭借原来的工作证,先去六机部开了证明。
没想到再去上海时,人家还是冷冰冰的。陈彭很无奈,“没有办法。你知道那时上海人是很排外的。”我很赞同。那年月,我正好也在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工作,天天要从徐家汇转车。在上海的公交车上买票,要是不说方言,一车的人都会齐刷刷地扭头盯牢你看。于是,陈彭赶紧改用纯正的上海话跟人家套近乎。这下,江南造船厂的大门才算是敲开了……当然,今天的上海,用其国际大都市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讲不讲上海话,都可以随意在浦西或浦东找到适合的工作。
创建机械专业,他们首先确立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和电力行业挂钩。诸如系统的动态测试、发电机、汽轮机的振动、共振,还有故障处理等。
这段时期,也有个小故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们准备安装一套从英国进口的设备,可申请实验室的报告一直未批。眼看着设备就要来了,陈彭毫不犹豫地拿出了 “桐城派”独到的思维模式,果敢地带着系里一帮人,把老电子楼一间半地下室里堆的东西清理出来,将设备安装完毕。待主抓教学的张瑞岐副院长回来后,面对这样的既成事实,也就首肯了。
谈起这件往事,陈彭开心极了。
他笑得十分轻松:“这么贵重的进口教学设备,总是要有地方安装吧?”这套英国制造的solartron动态测试设备最初的安装测试,还是困难重重的。为此,他有目的地出国访问学习,“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增长些知识。对自身的业务,也是学习和提高的机会”。他很认真地对英国的机械测试设备,做了前期的考察学习和了解。对于加拿大大学在学生大二时,才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选择专业方向,而且学生毕业前,就由用人单位来校选才,解决学生后顾之忧,使其可以安心做好毕业设计。陈彭以为,这样的培养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陈彭的工作越来越顺手了。他以为还有些时间,可以去实现更多的想要完成的事情。
1993年的五四青年节,学生组织请他去做讲座。那段时间,他已经感到身体不舒服。那天上午他很忙,可答应了学生的事情不忍拒绝。下午,他强忍不适,一步步登上楼梯。到了教室,讲了一半的他,突然不行了……21年了。从医院出来后,他的行走就一直很艰难。
今天,回过头来看,他和夫人都认为当初应该抓紧去检查,找出病因对症治疗,病情就不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可惜,那一代知识分子总是认为工作第一,个人的一切始终是次要的。
不过,对于陈彭老师的身体现状,老俩口很乐观。夫人说:“幸亏陈彭是栓在大脑指挥肢体行动区域。要是栓在吞咽部位,吃东西都难了;栓在发音部位,就不能清楚地讲话了。”
走得很慢的陈彭老师,为了锻炼肢体协调能力,开始学习弹奏电子琴,家里不时传出的乐曲,是他依然延续着青年时代对生活的态度。他开始学习书法、绘画,强制性地要求自己握紧毛笔,去抒发对生命的渴望,家里到处悬挂着他的作品,那遒劲的笔锋,是他顽强意志的体现。他还开始使用计算机,用网络联系着国内外的同学之情。
这些年,夫妇俩牵手去了海南,一住就是半年。那些日子,他们每天都要在海滩边漫步,在傍晚的斜阳中,在椰树下被微风轻轻地拂面。学校离退办组织出游,他们也积极参加,不爬山,就坐在山脚下,静静地品味着大山的气息,也是一种心情的放松。他们还一同去过鸟巢、森林公园。
我收起采访记录,看看时间,已经超出了1个半小时。我有些不好意思,陈彭反映真快,马上说:“没关系,还要表扬你。”没挨批?我有些得意,索性请他谈谈对人生的感悟。
他认为,用三句话就可以总结出人生的三部曲:一是路漫漫,上下求索。在年轻时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的阶段,要学会求索;其二是明方向,艰苦奋斗。一旦明确追求的方向后,就要努力去奋斗;第三则是晚年获果实,颐养天年。在有限的时间里,放松地休息养生。
陈彭家里订着几份报纸,有《中国电视报》、《中国剪报》等。平时他很关心时事,手头一直没有断过书籍。谈论起时下过度装修成风,他们认为家是用来放松的地方,一味地讲究奢华是没有意义的。我喜欢他们夫妇这样直接地表达喜爱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
还有,因为采访曾闻问老师时,她拒绝再使用院长一词。故而以此为范本,对今后所有卸任的院校领导的采访报道,一概称为老师。这是发自心底的尊重,也是一种平等的体现。
在曾闻问老师和陈彭老师身上,我也同样感受到了他们是把当院长的那段经历,作为工作中的一个阶段来对待和总结。就像季羡林先生对白岩松说的:“没有必要说我多么高尚和伟大,分工不同,我分到了这一行,怎么办?”
当这种平等和平视,成为我们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我们才会真正地开掘出所有的潜能,去将所从事的工作和事业的过程,视为一种快乐和美好。当我们每一个生活在校园里的人,在平等和平视中得到尊重和信任,那时的校园一定是最美丽和谐的。
陈彭老师的精力和记忆力都很棒。将初稿传给他后,我们对照着打印稿一起修改时,他可以凭借记忆去找出第几页的哪个字错了。陈彭也是极为严谨的。他一遍遍逐字逐段地仔细的审核校对,哪行那段哪句话有问题,他都不会放过。有的地方他有看法,就很委婉地询问:“这段写在这里会不会引起争议?”他表达观点时总是那样的温和、亲切,让人没有半点顾虑,你可以轻松地与他共同探讨一步步走来的事实。一次次电话打来时,他总是会问:“没有影响你休息吧?你吃饭了吗?”每次放下电话,都觉得很温暖。
时间都去哪了?当看着他和张老师眼睛花了,行动迟缓了。可依然将今天的日子过得这样平静、自如和享受,不由得不去佩服欣赏。他们平和地一路荣辱与共,至今还能相依相伴,去分享晚霞中金色的余晖。这样的人生境界,值得他们珍视和骄傲,也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