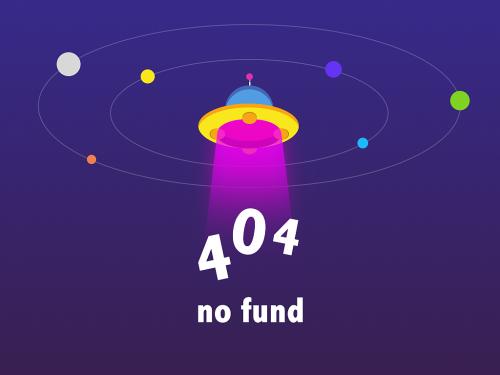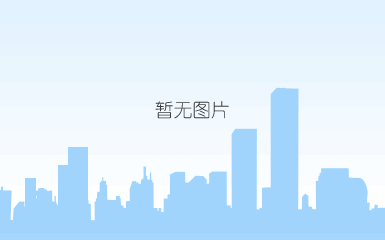这个夏日,在一场雨后的凉爽中,我来到京城北郊小营一幢十多年的老式塔楼502室。当我有幸安静地坐在这位儒雅的老人面前,听他用那依然清晰纯正的京腔缓缓诉说时,我突然觉得面前这位八十八岁的长者,不单单是三十多年前早就认识的动力系的老师。他,更是位用历经坎坷却始终积极向上的人生经历,撰写出极具个性并富传奇色彩故事的经典人物。
他,就是张保衡先生。
作为一位1953年走上讲台、1983年被评为终身教授、1999年离休的老教授,我们间的谈话很自然地从他的教书生涯开始。很想知道,教了一辈子书,最值得他自豪的是什么?
还是那副熟悉慈祥的笑容:“是认真讲课,是教书育人。”他认为教师要把知识讲活了,书本上的理论,一定要结合生产实践灌输给学生,才能启发学生的发散思维。同时应该常常问问学生:课堂上的这一小时,你学到了什么?在育人上,他很为自己带的不少已承担起教学、管理和企业重任的研究生骄傲、开心。说他们懂得学习专业知识,无非是一种维生的技能和特长,不能叫知识分子;读些文学作品,也不能说就有了文化修养。他们传承着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自检、自律、自控,是合格的知识分子了。
正如他的学生徐鸿回忆道:“听张老师的 《汽轮机原理》,生动、鲜活。他从不照着书本去读,而是深入浅出地将在现场碰到的问题、处理的方式,融汇到课堂知识中。”三十多年过去了,徐鸿说起当年的专业课考试,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考题有:汽轮机振动的十大原因?当汽轮机中间某级动叶片全部脱落,请分析该级前后两级叶片状态?在校部主楼f座六层能动学院的会议室里,徐鸿说起张先生的语气,充满着敬佩和感激。他印象最深的是跟着张老师,经常一天天啃着馒头泡在国家图书馆查找资料。
张先生的另一位学生付忠广介绍:“张老师的专著 《大容量火电机组寿命管理与调峰运行》一版再版n次了。几乎所有研究这个专业的人,都看过这本书。”因为“张老师在扭振和机组疲劳研究方向上问题抓得很准、水平很高、对学生要求也很严。”付忠广老师说他的硕士论文刚完成一汇报,张老师马上敏感地分析这种用新的手段解决“边界元”计算、“有限差分法”程序,其计算结果对整体工程很有用处。于是拿到美国华盛顿国际会议上交流,用此计算结果交换了“专用文献数据库”十年的使用权。
张先生在系里、在圈内、在电力系统,甚至国内相关学术界和企业界,一直以来被人们尊称为 “张汽机”。与“马锅炉”(同是动力系老师的马建隆先生)一并,已成为我们学校的知名品牌和响当当的名片了。
没想到追溯张先生从事汽机专业的经历,竟然要翻开尘封的史册,走回到上世纪的1942年。
从小聪慧过人的他,在北京四中毕业后,怀着工业救国的美好理想和伟大志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北京大学工学院机械系。发榜那天下雨,他的同学叫他一起去看榜。在班上一直考试第一的他,觉得根本就没那必要:“没问题,怎么会没我呢?不可能啊!”四年北大顺利毕业后,22岁的他,分配到石景山发电厂汽机专业。踏踏实实在干了四年汽机运行、两年检修,成为一名合格的汽机专责工程师。
这位京城有名的四代中医殷实世家的孩子,当时都挣到100多块光洋了。从新街口棉花胡同四合院的老宅到石景山发电厂,那会可没有快捷的地铁,常常只能是坐黄包车,上运行三班倒也够辛苦的了。不过,这会的张老师,十分肯定地强调:
“我这一辈子,都得益于石景山这六年扎实的专业基础了。”一直忧虑着学生现状的他话锋一转:“现在的学生不愿去现场实习,毕业生不愿去基层电厂。这将来怎么发展?专业知识也白学了?”他依然直率地认为:
“毕业生至少应该在电厂待三年,一毕业就去设计院、研究所。没有现场的实践经验,你设计、研究什么?当然,大学老师也一样,一定要去现场熟悉运行设备、系统,了解现场运行存在的问题、故障,你才有底气站在讲台上解答学生问题,才有可能把知识讲活了。”
我知道,他是用自己一生积淀下来的成功的教学和科研经验,在坦诚地提示和警醒着现实和我们!我知道,即便已经耄耋到一头银发、腿上楔上钢钉,他也无法泯灭胸中从青年时代就一直在燃烧的拳拳报国之情。
因为,他所有的科研项目方向和成果,都来源于对现场生产实践敏锐的发现和捕捉,前瞻性地对相关国内外资料的研究和信息整理。比如:汽轮机大机组热应力疲劳寿命分析、预测、监控及管理的研究;比如:汽轮机汽轮快控及轴系扭振在线监测;还有:大机组调峰特性及启动优化;轴系热疲劳裂纹扩展预测;调峰机组负荷分配优化;老机组剩余寿命预测等。
去年,老先生亲自查了800多份有创造性的毕业论文。但让他深为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没能进一步推广到实践中,形成生产力的太少。他认为研究生的论文不应该单单是以发表为目的,那样科研成果就死了,太可惜。
当年张老师几乎每年用六个月的时间去现场。从北京的石景山电厂、东郊热电厂到河北唐山电厂、内蒙元宝山电厂、上海的闸北电厂、东北的大连电厂及华能电厂。吃在职工食堂,住在电厂招待所。那些年,他还到各地举办有关大机组调峰、轴系扭振等讲座五六十场。加上一些论文、项目的评审,有时一天要赶几个会议。一次,坐夜车从东北赶回北京,九点准时参加了中国电力编辑部的会议。当时的电力部长也被感动了,向大家介绍说:张老师是连夜赶回来的呀!还有一次,从上海当天赶到武汉,晚上又赶到青岛,再接着去了无锡。现在说起这些曾经辛劳和疲惫的奔波,老先生还是那样平静:“人,就该这样!”
文革中,他这个 “反动学术权威”、又是有两个台湾国民党军官弟弟的哥哥、再加上世袭四代中医世家的背景,被批斗、被折磨和殴打就是家常便饭。可在80年代学校恢复评职称时,作为评委的张老师就没说一句“那些人”的不是,相反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能做到这样的大度和大气,需要多大的胸怀和宽容啊!听说有的人还曾用藤条抽打过他的。
这个夏至后的日子,老先生的面庞在窗外阳光的折射中显现出剪影的效果。他苦笑着摇摇头,已经不愿提及这段经历了。他还是那样均匀的语速:“过去的都过去了,结果好才是最重要的。”接着补充了一句:“这是托尔斯泰的话。”
他非常惋惜被剥夺工作权利、白白荒废的文革十年的时间。他计算了一下,耽误的十年,得用每天多干的四个小时去弥补。这样,十年补上五年,二十年就可以补回来十年的光阴了。那些年,无论在家还是去现场,他基本上是晚上十二点后才睡觉。
在《华北电力大学校史》资深教授介绍中,张先生历任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汽机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电力部热力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汽机组副组长、《中国电力》及《热力发电厂》编委、清华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委员等职。主要科研成果汽轮机疲劳寿命项目、大机组汽门快控及轴系扭振特性项目分获电力部技术进步二等奖;国家攀登计划b项获国家科技二等奖;1991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他在电管局参加的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负责起草的我国电业技术人员、技术等级标准、电业无事故奖励、超额奖励、合理化建议奖励等,经全国电业会议通过,成为我国电力生产管理的正式文件。
学校研究生部恢复初期,他和十多位教师在12年时间里培养了400多位研究生。那时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苦。他充分发挥和利用学校的人才条件,尽可能地挖掘历年与发电厂的合作关系,相继开发了17个科研项目,探索出将科研成果与电厂现场实践相结合,成功培养学生的新路子。
老先生在他的同代人眼中,是个热心、善良的人。王家璇老师一直称呼他为老哥哥。碰到一些工作和生活上的事,喜欢找他拿拿主意、出出点子。几位动力系主任都在多种场合说过:张老师对动力系的学科发展,功不可没。
在学生眼中,他更像一位独具人格魅力的长者。在保定我们与他的学生们电话联系采访时间,一听说写张老师,他们马上很热情地表态:是应该好好写写这些导师的风范,他们是学校厚重的精神财富和支撑。最让徐鸿钦佩的是老先生不仅仅是课讲得相当精彩,相继带了38个研究生。最大的贡献在于早在八十年代初,就率先注重科研项目与现场的生产实践相结合。他开创了高校与电力企业科研项目横向结合的先河;他在电力企业拥有较高的声望和不可替代的宝贵价值,他与企业界专家有着很好的关系和广泛的人脉。
开创先河、不可替代、功不可没,用在老先生身上,大概不是简单的评价和赞誉了。那是一步步厚重历程的记录、是一段段奉献才智的总结。
而他与同事、朋友间的兄弟情;与学生间的师生情,是已经延续了一辈子的真挚情感。
这个下午,徐鸿用他那具有磁性的语气、用很“老舍”的京城口语,抱着一个大大的茶杯,如是评价着张先生:他一生勤奋、执着、聪明;他做学问具有导师的风范,是做“通”了;他做人大气、大度和善良;他为人处事很随意,从不摆谱;他有口吃的就饱了,很节省,可随便穿什么都有派;他能做的尽量自己都做了,是个活明白了的人。他去宿舍跟学生聊家常、在现场干活亲历亲为……徐鸿诠释着老先生的聪明,是把热动领域和物理学融会贯通了。比如:老先生一看原理图,能从物理学的流体、声、光、电中,正确地分析判断出对与错。而他本人受益最大的也正是抓住基本的物理概念,运用到不同的学科领域,融会贯通。留学德国八年的徐鸿认为,在他接触到过的国内和德国的老师中,能这样运用物理学基础去分析、判断事物能力的老师,实在是凤毛麟角。
一次,他和张老师一起去看车展。人家介绍说法国的雷诺转弯半径1.5米。张老师淡淡地问:轮距是多少?然后,张老师指出:肯定不对。那些人支支吾吾地辩解:法国人就是这么说的。张老师火了:这不可能啊!你计算一下。最后人家专门去查了资料,又特意来道歉说:是错了。
张老师在许多评审会上的大家风范,也很让弟子们折服:他从不让人下不来台。但,又从不轻易放过存在的问题。总能用几句委婉的话,阐明观点和看法,从而博得评委们的一致赞同。这么多年的各类评审活动中,没听过张老师说过什么露怯的和多余的话。
2004年的5月,校园里的花开了、草绿了。
校部大门口打出了这样一行大红的祝福:热烈庆祝张保衡教授八十寿辰!为此能动学院还举办了专场学术报告会,300多人与会参加了老先生八十寿辰的系列庆祝活动。这种轰动校园的祝福,能不能“绝后”不敢说,至少这样的规模、牵动了学校和企业界这么多人士,“空前”是毋庸置疑的。
先生,是位睿智的学者、率真的人生导师。先生,也是位需要我们在浮躁的今天,去静下心来慢慢解读的大家。他穷尽一生的教学、科研生涯,是一位知识分子用才智、用心血、用极富激情的生命年华,实现了培养学生、服务电力事业、报效国家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在京城夏日难得的清新里,不舍地和先生告别。走到长廊的尽头,回头望去,在宽敞、悠长的楼道里,他的身影依旧是那么挺拔。
张保衡先生的人生,颇具传奇色彩。
年轻时家境好,人又聪明,读了北大。毕业去了石景山发电厂职业不错,薪水也挺高。在那年代玩个骑马、射击,在京城可不易,得有条件。本该一帆风顺、风流倜傥一皇城根的帅哥,谁曾想文革中遭了大难。1971年至1974年间,他以反动学术权威的身份,又加码被整成反革命,下放到了河北农村。
那时,这只掉了毛、落了难的凤凰,除了每天在日头的暴晒下,与农民伯伯一起种地除草,还捎带着兼职负责修理全村人家的收音机、缝纫机、闹钟。
一年春旱,村里的四台水泵坏了三台。地里的麦子等着浇水,这可急坏了村长。问他:“老张头,你会鼓捣鼓捣吗?要什么条件,赶紧的说。”他心说这些水泵咱在电厂早就修过,还不是和玩一样。可他得夹着尾巴啊,于是回答:“那我试试吧!不过得叫电工给我当助手,去买铜线缠电机线圈。”结果,他俩整整忙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要送电试试了。他还有精力和心情逗那电工:咱得烧烧香、磕磕头吧?嘿!三台水泵,可够给争气的,全部正常运转起来。把个村长给乐得直嚷嚷:“歇会,快歇会!早包好了饺子等着你呢!”
不过,这事还不算太神奇。
一天,这位“张老头”在地里干活。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公安员。在地头就吼着嗓子叫唤:“谁叫张保衡啊?”村长和乡亲们紧张极了,以为这老张头又出什么事了?那公安把他带在车后,出了村才悄声说:“听说你会针灸。咱县公安局长的爹病重了,让你去瞧瞧。”
这被管制的 “老张头”去了后一看,晚期食道癌病人。老头已经七天不能吃东西了,人瘦的干黄干黄的。公安局长孝顺,带着爹石家庄和北京都去瞧过了,医生给了话,最多还能活三个多月。这平日里在村里给乡亲们扎扎针,治个头疼脑热的他,那会一下子竟然回想起父亲说过这类病人,首先要让他吃东西。记忆中父亲的药方是薏仁米加威灵仙熬粥,吃一个礼拜。
两周后他再去时,老爷子体力已经有所恢复,也能吃东西了,后来整整又多活了一年半。那个当局长的儿子给已经离开那里的他来信感谢:“老爷子让一定要对您说声谢谢!说是您给了他一年半的寿数。”我听着这事时忍不住哈哈大笑,问他:“您够神的。那您系统地学过中医吗?您怎么就胆敢给人扎针、治病啊?”88岁的老先生,透着那股子聪慧特自豪:“我耳濡目染的也熏点家传吧!”兴许这也就是他的弟子们口中所说的少见的聪明劲吧!
我都想象不出,天底下还能有谁还能将这般沉重、无望的悲惨生活,过得如此有滋有味、积极向上?就这样,在他平反离开村里时,那年月啊!村上的贫下中农们,竟然敢给出这种鉴定:这样的反革命,多给我们送几个。
其实,老先生一直是位十分浪漫阳光、热爱生活的人。年轻时,他喜欢骑马、射击、摄影、玩虎伏(一种人在里边撑成大字形的旋转滚轮,老辈子的叫法)。如今家中客厅里的沙发、地毯的暗红色也是他选的,家里楼上楼下的墙上到处是他和夫人柳老师年轻时代的帅气的照片;儿子、女儿在国外的家庭生活照。
现在的他,还很牛气地自谓是“京城第一馅”。什么饺子、包子、馅饼,只要是带馅的,瞅他那神气劲:“我做得肯定是京城最棒的。”此外,炖肉、做鱼,那就是十分钟的小事。家里洗衣服、打扫卫生、做饭,基本上是他的事。夫人心脏不好,他舍不得她劳累操心的:“你就在家弹弹钢琴,跟着贺老师她们唱唱歌。”他说自己干家务是最好的锻炼身体。
中午了,老两口非要请我们吃饭。过马路时还不让搀着:“我没事。”呵,敢情,饭店那一层层台阶,老先生利利索索地就上去了。一只烤鸭、两份蔬菜。老先生和夫人胃口都不错,属于吃嘛嘛香。剩了些,很自然地分类打包,拎着回家。
对,是他的学生徐鸿说来着,这叫:不摆谱,很节省。
你想啊!曾经在乡村里被 “改造”过,老先生知道那粮食、那蔬菜都是怎么长出来的?浪费,那是作孽!摆谱,那是暴发户们才干的。
就这样,88岁的老先生,穿着随意简单,活得明白自由。把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生的领悟和理解,精彩到了生命的晚年。
那,我们就祝福老先生健康、长寿;还有一直这样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洒脱、率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