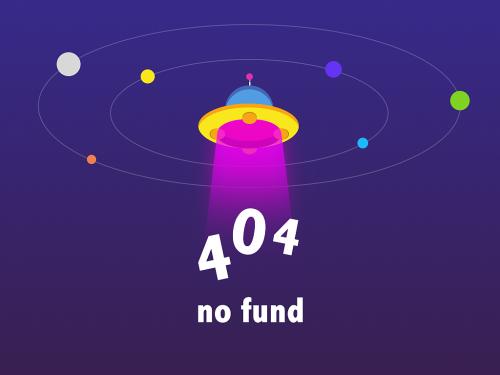白描曾闻问先生-37000dcm威尼斯
作者:丁清 供稿单位: 发布时间:2013-08-28 浏览次数:
我就是一个“教书匠”,很高兴自己教了一辈子书。我的行事、为人,主要来自家庭影响和中学教育———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被不断否定的“烙印”。庆幸八十年代后能回归自我,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曾闻问
曾闻问,汉族,湖南长沙人,1930年11月生于南京。中共党员,教授。1952年毕业于贵州大学数理系。1954年调入北京电力学校工作,1958年后进入北京电力学院工作。1981年至1983年前往美国西东大学(setonhall)作访问学者,进行函数论方面的研究。1983年至1990年担任华北电力学院副院长。曾任北京市海淀区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河北省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1991年被评为教授。其论文《因材施教分级教学》、《用英语教授高等数学的实践和成效》分别获得1989年、1993年河北省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1990年、1992年分别获得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优秀老教育工作者奖、优秀教育工作者奖。
曾闻问先生,是我校从1958年建校伊始至今,唯一的一位女性院领导;是因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培养青年教师出了名的严师;是主管教学时,推行分层次教学、英语教学的倡导者;是一贯坚持原则,绝不向权势妥协的领导;是在1978年48岁那年,参加出国英语培训考试,在同时参加考试的我校教师中成绩最高那位;是学校搬迁到岳城水库时,干过一年托儿所阿姨的人;是从清洁工到普通教师、教授,众多人口中的好人。
2012年的初冬,我就造访过她。电话里,她那么热情:“好久不见了,欢迎你来北京!”
可当我正儿八经地拿出纸张,要记录我们间的谈话时,她很干脆地帮我把夹子塞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海阔天空地聊了半天家常。出来时,站在京城冬天的马路上,恍惚地看着穿行往来的车流,我晕了。很不甘心地问自己:我来干嘛的呀?
回到保定,我开始不停地往她家打电话,经常是对着可以留言的话机自说自话。每次她都回话给我,当然也没忘记狠狠地批评:“你以后不要叫院长了,我已经不当院长了,不然就不理你了。”我狡辩:“没有吧?”那种不容申辩的口气,感觉她的性子比我还急:“我这可有录音呢!”只好拿出我的诚意保证:“以后一定只叫老师。”后来跟她商量:“北京校区的吴素华老师希望采访时能留下影像、声像资料。那能否带着摄像一并去。”没什么商量的回答是:“那我就把你关在门外了。”我可不敢冒这种风险。
2013年的春天,京城很美。景山和紫竹院的牡丹、芍药姹紫嫣红;植物园的郁金香色彩缤纷。我告诉她:“我已抵京,随时等她有空过去。”去了那院子,忘了是几单元?正翻包要查,听见她大叫:“丁清,在这儿呢。”原来她在窗前看着我。
其实,我没怎么跟曾闻问先生打过交道,我都不记得是否与她说过话。可,怎么一点陌生的感觉都没有呢?一点隔代人的疏离也没有呢?竟像是好多年前就是朋友一样的熟识和亲近。
这次不能再跑题了。
我抓紧问:“您当院长时,是什么心情啊?”先生爽朗地笑起来:“什么心情啊!那是个‘历史的误会’,照湖南谚语说就是‘狗戴帽子,碰中的’。”她解释道:“大概当时要求的条件是出过国、女性、非党员。套来套去的,条件都符合,就套上我了。”
这怎么可能呢?如果真是个误会,那真是个非常值得庆幸的误会。
北京电力学院,是在北京电力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建立的。先生在电校时就担任了数学教研室主任。1958年学院成立后,她继续担任教研室主任。1959年,数学教研室被评为北京市文教先进集体。
在教学上,先生的认真,是许多教师的共同感受。就拿《高等数学》来说,无论教了多少遍,每学期上课,她都还要重新备课,新写教案,做没做过的习题。如今已经退休的数学老师王俊荣回忆:那天,在教研室曾先生问:“小王,你做了习题了吗?咱们对对答案吧!”王俊荣老师说当时很有些惊讶:“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曾闻问这样的老教师了,还做习题,还跟我对答案?”
另一位数学老师董凤荣清晰地记得:“那时候,我们教研室经常组织教学研讨会、学术讨论会,由教研室评论小组对青年教师的试讲进行讨论,大家也就不同的学术观点进行争论。学术氛围非常浓厚,气氛特别好。曾闻问老师当了院长后,还一直坚持在第一线上课,经常回来参加这类教学活动。”董凤荣老师还专门评价了先生的自学能力和虚心学习的精神,对在过去大学里没有学过的课程,“曾闻问老师在通读自学后,还放下架子,去听年轻老师的课。”
邢良瑛老师在1980年时,担任过曾先生的辅导老师。夫妇俩是先生一直往来的好朋友。邢老师语气很温和:“曾闻问老师,讲课条理特别清楚,办事很细致,对青年教师要求也很严格。她从讲什么内容到怎么讲,都会对青年教师提出具体要求。此外,曾闻问老师还一直要求任课老师自己要先做习题,有的放矢地布置作业。”邢老师补充到:“你可别以为她只是要求?你可别以为她只是要求?河大分来个研究生,不知道曾闻问老师的认真劲,结果被发现没有做作业,挨了批。”邢老师还记得曾先生平时经常交代:“对学生要求一定要严格,这是对他们负责。”一次,有两个班的学生不交作业,邢老师如实告诉了先生。曾先生就去找学生一个个谈话,询问情况。
为了提高教学水平,了解国际数学教学进展,曾先生还主动筹资去香港买英文教材、磁带。当时,钱实在是不够了,先生就拿出自己的美元凑上。邢良瑛老师很感动地谈到:“她回国时,给我们教研室20多人,都带了小礼物。”
稍事停顿,邢老师加了句:“对了,她现在不许我们叫她院长了,谁叫跟谁急。”我笑了,原来这是条人人平等的规则。闹半天,她是真的不在意这官衔带来的、被一些人很是看重的、哪怕是曾经的地位。正因为先生的这种旷达心态,才使得她在离开领导岗位时,没有什么“失落感”,也没有那种“人走茶凉”的感受。
管保国老师则强调:“我明显地感到的是曾闻问老师出国前后,在教学理念上的改变。她一点都不保守,很愿意接受新的教学方式。”管老师几次重复:“她人真好。你一定要转达我对她的问候!”
从国外回来后,先生对一线教学改革做了大胆的尝试。结合当时的学生学业状况,按a、b、c分班,在基础课中推行分层次教学。高班的基础课程,实施外语教学。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的论文 《因材施教分级教学》、《用英语教授高等数学的实践和成效》,记录了先生这段教学改革的体会和收获。
作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她无法回避的是全院的教学秩序、教学文件建设和教学质量提高、培养合格人才的全盘工作规划和教学管理工作。
当时,我国高校教育从苏联模式转向 “学分制”。不再是没有个性的“大一统”人才的培养。学生在保证基础课程学习的前提下,有了自主选课拿学分的自由。教育部的这些改革措施,非常符合先生的教育理念。她自己和那几代大学生求学的成功经历,就证实了这种教育体系的人性化和合理性。所以,先生积极地推行这种教育模式。
谈起那时的工作感受,先生说:“其实,当时的感觉是接上了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为此,先生还很幽默地问过时任院长王家璇:“现在这么做,究竟是‘创新’,还是‘复旧’?”王家璇院长很有水平地回答:“何必‘定义’呢?只要对培养学生有利,做就是了。”
但,学校教学秩序的维护,学风建设的坚守,却不单单是学校自身的事。
某位部领导的孩子,在南方一所大学被退学后,却很气势地带了份“院长办公室”开的“转学证明”要求转入我校。按规定转学证明应由教务处开具,我校当然不能接收。那位领导只好找到先生说:“就是因为拿不到正式转学手续,才请你们通融的。”南方那所学校的教务处也有些“死心眼”,就是不给开正式转学手续。于是,先生很明确地表态:“没有正式手续,我们也无法通融”。后来王家璇院长告诉她:某司长曾为此专门打来电话,让他办理此事。王院长的回答是:“那请司长亲笔写个条子,我们可考虑办理。”面对这么“拎不清”的两个“书呆子”院领导,那位分管部属院校拨款的领导,当然心中很不爽。事后,王家璇院长用颇为遗憾、加上几分嘲讽的口吻告诉她:“咱们这么坚持原则的‘好处’是,几十万元的款项被另一所收了那学生的学校拿去了。”
……问她:“面对这类无法言说的事情,您对当时的决策,后悔过吗?”
她坚定地回答:“我不会改变做法的。不然,我还怎么要求各系去抓学风建设。我不能首先带头去破坏学校的教学秩序吧。”
树立良好学风,严格要求学生,是先生在中学时代就形成的理念。
抗日战争时期,她跟随家人逃难。从南京一路颠沛流离到了贵州湄潭。当时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已在那里稳定下来,并办了附中。浙大的校训是“求是”,学风严谨。
1942年,先生考入浙大附中。在附中任教的老师,多是浙大优秀毕业生。如今老校友聚会时,同学们无不认为之所以能在工作中有所作为,全是那时打下的坚实基础。当年任课的英语老师,是从旧金山归来的华侨。老师让学生们背英文课文,唱英文歌。所以三十多年后,先生认为她能顺利地通过出国考试,完全得益于当年的英语教学。
在决定是否出国做访问学者时,她有些犹豫,她自谦一直教书,没研究过什么课题,担心完成不了教学研究任务。于是,很信任地征询读附中时数学老师孙嗣良先生的意见。孙先生依然那么真挚:“闻问,有两年时间静下心来读读书,不是挺好的吗?”在老师的鼓励下,出国期间,她努力读书,参与教学任务,尽可能地做了一些研究工作。
浙大附中不仅重视国语、英语、算术这些主课,对体育、音乐、图画、劳作等课也不放松。考试分数能到70分就是高分了,80分以上的寥寥无几。浙大还利用天然条件,在湄江边用竹竿围起一个长方框当作游泳池,让不会水的学生们在框里学游泳。先生回忆:“那时老师好,学业负担也不重。学习知识的同时,玩得很开心。真不知道,现在的学生怎么负担那么重?学得那么累?”
谈话间,她的大气、从容和不时从口中带出的格言,隐约传递出良好家风的底蕴。说到曾经对父亲的“批判”,先生心怀着深深的愧疚。她说:“年龄越大,越觉得爸爸对我潜移默化的影响很大。”
先生的父亲毕业于东南大学(入学时叫南京高等师范,不久改名东南大学,后又改名中央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父亲在南京办了一家“和平铁厂”,是一个小规模的作坊。父亲自己设计,工人们在车间加工,做一些有特殊要求的产品。生意不错,家境也不错,有不少亲戚来投靠。所以,先生从小就认为爸爸是个 “有本事”的人。父亲做人的原则是做人,就要靠自己,不要去求别人;没本事的人,才去求人。要自给自足,不能搞歪门邪道。国家危亡,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力助人。
童年时,家里挂着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她随口背出:“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种勤俭持家的家庭氛围、珍爱粒米寸丝的传统信念,她熟记于心,至今影响着她的生活。
从手中一寸长的铅笔头,到用废纸反面打印的名片。从阳台上挂着自己缝制的洗的洁白的小紫花手帕,到上课时还穿修补过的衣裤。那铅笔头握不住了,就套上旧钢笔套接着用。家里的家具,都很陈旧了,桌椅是学校作价的旧货。如今居住的房子,墙顶端的石膏线已经脱落了一部分。可她觉得:“没什么啊!这不很好吗?”
现在的她,依然单纯得可爱。谈到父亲,总是用口语爸爸。说起当年的老师、同学,依然像是中学生那样向往。
去年做白内障手术时,她对医生提的要求是:“做完了,你还要保留我的近视。”她的理由是:“我戴了一辈子眼镜,不近视了,反倒要配老花眼镜,会不习惯的。”她依然保持着以前的生活方式。我的理解是,她平静地接受着生活中的种种不完美和缺憾。
1952年工作后,她试图摆脱家庭的阶级烙印,一直在深刻反省批判着自身的不足,由衷地感谢中国共产党。希望通过提高认识,能够入党。经过肃反、反右后,她有些迷茫。清华大学毕业的数学教师,究竟为什么会是右派?开头还是带领大家学习的组长,转瞬就成了右派,更让人糊涂。所以,她只能检查是自己觉悟太低,看不出问题。再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四清运动,直到文革……先生坦率地承认:在走了些弯路后,我们应该重新认识那些本就铸就在我们民族血脉中的优良传统和做人准则。
想起她还当过托儿所阿姨一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段时间,学校刚刚由北京搬到岳城水库,军宣队领导要开展活动,组织大家学习,得先解决孩子问题,就决定办全托托儿所。由雷柏青和王秀芝做负责人,找一些教师做 “阿姨”,曾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有的人对此很不屑,可曾先生一干就是一年。在她的眼中,没有什么职业和工作的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这事是不是值得去做。聊起这事时她还是那样的潇洒:这有什么啊?不是挺好的吗?
性格开朗,非常爱笑,似乎从没有什么烦恼的先生,在院子里碰到清洁工人,或者是孩子,都一样的亲热。更不要说对曾经教过她的老师、她教过的学生,还有她中学的同学。她无论做官还是为民时都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这是大家普遍的评价。
两次在先生那,她都特意让我看了一张老照片。
那是一张珍藏的拍摄于1962年的合影。八位1952年大学毕业,1958年同时到北京电力学院的老师,为了纪念参加工作十周年,专程到天安门前的留影。
对此,先生一再说起的心愿是:“当年我们一起毕业的十多个人,从电力学校到电力学院,如今有的调走,有的故去,就剩下我和高之樑了。能不能抓紧采访一下高之樑老师,或者采访已故老师的同事和亲属。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多为学校留下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不然,就无法挽回了。”白描,《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文字简练单纯,不加渲染烘托的写作风格。”将基调定在以这样“简练单纯”的笔法,去完成一个学校许多人数次叮嘱我的 “这是个好人,一个非常正直的人,一个值得好好写的人”。我问自己:是不是有些轻率呢?
其实,我倒很一厢情愿地以为:白描所谓的白,不仅是单纯,它应当涵盖的情感,还有纯洁、清新和明快的意义,应该是符合曾闻问老师这样的人物个性和形象的。
先生,给我留下了这样深刻的印象:简单、坚毅、同时又很大气、洒脱。这与年龄无关,是一个人家庭或是家族的烙印,标记着先生成长的历程和血脉的沿袭。
先生,用她的开朗和激情,用她的正直和率真,将83年的生命年华渲染出青春的味道。先生的人生轨迹,让岁月的轮回绽放出夺目的光彩,温暖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