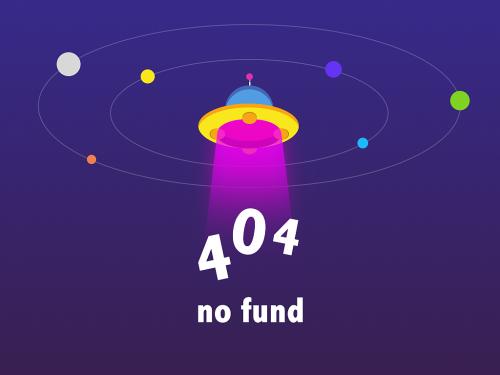我从小就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大学本来该读文学系的,只是因为当时国家急需建设人才才转了行。不过,我现在依然认为:学工科的,多读点文学作品对启迪思维有好处。我的不少专业知识,基本上是靠自学的,这得益于大学扎实的基础课程学习。———顾慰慈
顾慰慈,男,汉族,1931年4月生于江苏无锡,中共党员,教授。1953年毕业于云南大学。1953年起在水利部、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华北水利水电学院研究生部、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动力经济学院和华北电力大学工作。1983年担任系主任、河北省水利学会理事、北京市水利学会理事、北京市高等学校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全国监理工程师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出题组成员。主要研究土工建筑物稳定性、工程项目管理。发表论文50余篇,核心期刊论文8篇。主编全国通用教材《水利水电工程管理》,译著4本,专著7本,编著职业培训教材1本。曾获水利电力部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次、三等奖2次,技术情报三等奖1次。两次荣获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先进教育工作者。
人说:江南是山多、水多、才子多。这绝不是妄言。比如,这位能将今天俭朴的日子,过得如此雅致,身上到处洋溢着君子味道的顾慰慈先生。2012年的岁末,京城已是一片冬日的凋零和寒冷。
在马甸桥东300路的公交站台上,茫然地看着北侧大片错落参差的楼群。这是片当年回迁已30多年的楼群,哪有空就在哪盖,排序也很混乱,外人还真不好找到这个拐弯抹角在旮旯里的27号楼。
只能依顾慰慈先生的话,在那等着……好在事先做了“功课”,对先生留在“校史”上的模样,多少有点记忆。于是,迎着一位清瘦得略显单薄的老人,我很自信地叫了声:“顾老师。”先生穿的还是在“校史”照片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的确良中山装,衣服上的风纪扣扣得牢牢的,脚下是双黑色布鞋,没带围巾、手套、帽子,甚至没穿棉衣。
先生步伐很利索,我只能加快速度紧跟着。
打开13层的房门,厅里摞着一屋子的纸箱子。
问先生:刚搬来吗?
先生很平静地回答:“不是,这是租的房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搬,索性就不拆箱了。”厨房里没有什么厨具。
卧室靠墙堆着些箱子,床上是空空的床板。厨房角落上没有启动的冰箱,一看就是房东原来的东西。
看到我一脸的疑惑,先生解释说:
“学校给的房子在这楼内,也是这样的两居室。现在是表弟几口住着。多年来,他们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现在我每天过去吃两顿饭,晚上在一起看看电视。”
我们就在这样的纸箱堆砌的高墙下,开始了谈话。
在先生缓缓的叙述中,一条清晰的人生轨迹,慢慢地幻化成淡雅的画面,展现出来。
1953年大学毕业的先生,被分配到水利部设计局。
当年,正是全面学习 “苏联老大哥”的高峰期,国家要统管所有水利设计。为此,国家从有关院校调集了200多人,集中学习三个月等待安排。后因计划变更,先生被分配到北京水利学校任教。中专授课任务重,要教三个班。一个礼拜每天上午四节课,天天晚上要备课到12点以后。
1958年北京水利水电学院成立,先生被安排在水工系任教。
那时,学校实行苏式教育,要求必须在45分钟时讲到某章节,还要事先预想学生的提问。现在回想起来,先生以为这种教学方式过于教条,中专的课还行,但不太适合大学的课堂。
文革中,少言寡语的先生,受到的冲击不大:“反正教师都挨批判。”
但,最令先生心痛的是书和研究资料的丢弃。
林彪的“一号通令”下达后,要求水电部学校20天搬出北京城,到岳城水库办校。先生是1969年底的第一批,今天接到通知,明天就必须离开。说到这,先生的语调顿时分外沉重:“临时钉的木头箱子,放不下多少书。床上满满的书,只能扔了一大半。书稿也都扔了。”虽然,44年过去了,先生始终无法抹去当时心头的痛楚。
原来由水利科学研究院、北京水利水电学院和华东水利学院组织合编的《水利水电工程名词词汇》,先生已经写了近10万字:“好几百页,厚厚的一摞啊!全扔了……”无奈地叹息后,先生还是那样舒缓地说:“有关“土坡稳定性计算”的论文,投给《土木工程学报》,已接到刊登通知。文革停刊,也没登。”对于一个潜心研究的知识分子,这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
杨绛在《干校六记》中回忆:当时,她时常可以从自己的改造地,路过钱钟书的菜地去邮局,两人有时还可以很幸福地在菜地边的窝棚里聊会儿天。杨绛很珍惜这样难得的聚会,向往地问:“咱俩要是就这样在这窝棚里生活,也不错嘛。”钱钟书看看四周不甘地说:“那还得有书。”
这些知识分子,你可以把他们从舒适的家中赶出来,可以不让他们在斜阳里品茗一杯浓郁的咖啡或清茶,可以驱赶他们踉跄着在田头劳作,甚至可以剥夺他们的尊严,侮辱他们的肉体,却不能夺取他们渴望与书为伴的心愿。
钱钟书、杨绛如是,顾慰慈亦然。
好在文革在“就是好,就是好!”的吼声中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老百姓还是要吃饭,还是要修小水利工程。
当时,几百名师生,来到河南林县。那里1958年建设的南谷洞水库已经漏水,隧洞也正要进行改建。这批下来接受“再教育”的水利院校师生,正是工地急需的专业人员。于是,军宣队和工宣队指派三名老师 (先生是其中之一)和三个学生上到水库工地。
他们一边协助当地进行水库改建设计,一边继续接受贫下中农对这些“臭老九”的再教育。上午整整四个小时抬石头、挑土的小工活,下午再干测量、设计的活。那两位老师负责大坝改建设计,先生的任务是隧洞的改建设计。
先生的设计方案是在隧洞进口处修建阀室,设置阀门,控制水库的防水、泄洪和蓄水;在阀室的侧面修一条40米深的竖井,直达山坡顶面,可供管理人员出入阀室。另外,对隧洞洞身增加钢筋混凝土衬砌,以防上部破碎岩石坍塌。同时,在隧洞末端设置消力池进行消能,防止放水时水流对下游渠道的冲刷。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勘探、设计,并由当地技术人员和农民的出色施工,圆满地完成了预期任务。
回到邯郸不久,先生又被派到武安,和其他两位教师一起,承担了一座引水式小型水电站设计。先生和同事们,在农村实地调研、勘探、设计八个多月,完成了这项工作。先生以为,这段时间的劳动让他学习了不少生产实践知识,还是很有益处的。这些知识的学习,对以后的讲课也很有用:“虽然讲的是理论课程,可脑子里应该清楚的是水库施工的工期、当地土壤、自然条件等。”
1973年,水工系招收了首批工农兵学员,规定专业课要进行现场教学。
军宣队、工宣队带着30多名教师和40多名学生一起,来到位于满城县大清河南支界河上规划修建的土门水库。当时正值冬季,天气很冷,教师和学生都只能住在农民家里。先生和另外两位老师,住在冰冷的粮仓里,只能临时用旧报纸糊上窗户挡风。屋里尽管也生了火,依然冻得手脚冰凉。课堂是农村小学寒假期间闲置的教室。在土门,教师们每天早上天还不亮就要起床集合,跑步一小时。早饭后上课、学习,晚上给学生辅导。寒假结束,没有教室了。全部人马辗转到保定,借用河北农大的两间教室,一间做宿舍、一间做教室,将课程上完。
当年,土门水库准备修建土坝。先生不顾天寒地冻,把学生带到现场,结合实际讲授土坝工程。土门水库那时正在设计尚未开工,还不存在的工程实体。为增加学生对土坝工程的感性认知,先生不辞辛苦带着学生来到保定周边的西大洋、洋河、王快等水库等参观学习,结合工程实际进行现场教学。想来当年这些有幸聆听了先生现场教学的学员,会终身享用先生严谨的教学学风和务实的工程设计理念。现场教学结束后回到岳城水库,先生又给学生补讲了水闸枢纽、重力坝、拱坝、支墩坝、隧洞工程等课程。
1974年到1975年间,系里承接了南铭河铁矿改河工程规划设计任务。
邯邢(邯郸、邢台)钢铁基地南铭河铁矿,隶属当时冶金部22冶所。铁矿位于南铭河一段河床的下面,每年洪水期都有被淹没的危险。因此这项改河工程,是南铭河铁矿采取的重大防洪工程。
系里将此项任务交给了先生等四位老师。接到任务后,先生首先到现场进行查勘和资料收集,并组织了工程现场地形测量、工程地质调查和洪水调查。同时对工程进行了全面考虑和规划。最终确定了改河防洪工程整体方案:在铁矿所处河段的上、下游,各修建一座土坝,将该河段的河道截断。然后在该河段的左侧河岸上,另外开挖一条人工河道引水、泄洪到南铭河下游,达到确保南铭河铁矿的安全。这个建两座土坝、开挖一条人工河,将河水引向下游的方案。体现了先生丰富的想象力,也是集先生多年专业知识的智慧结晶。
那天,先生把图纸挂在墙上,解释了自己的设计思路和方案,并将所有设计说明书和图纸交给了邯邢钢铁基地管理单位。他们非常满意,毫不犹豫地付给系里10万元设计费。
我曾经的自动控制系统专业,离先生的专业太远,时常听不懂先生的专业术语。于是,我很不好意思地常常打断他的思路询问。先生总是很耐心地停下来,慢慢地重复那些地名和专业词汇。有时,索性画出草图来解释。
比如说明这个铁矿的引水方案。先生先画了一条宽宽的河,在两端上下游标注出筑坝拦河的地方,而后从中间部位再标示开挖人工河引水的地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对一个完全外行的我,用这样直白的图示,将这个引水工程注释得如此明白,你不得不佩服和欣赏先生的教学水平。
1976年,先生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讲授了水工建筑课程。
1977、1978年,先生在邯郸给两届本科学生上课;1979年开始带研究生,担任水工教研室副主任;1982年初调到北京研究生部。
1983年10月,在北京水利水电干部学院、北京水力发电学校和华北水电学院研究生部三家单位的基础上,合并成立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学院含大学部和中专部,大学部设两个系:电力系和水工系(水工系含三个专业即水利工程管理、施工机械管理、物资管理)。
北京水利电力经济管理学院成立后,高之樑为院长,李正、南新旭等3人为副院长,任命先生和于之江为水工系负责人。对于这一任命,先生的想法是:自己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只适合具体的教学科研工作,不太适合担任领导。所以任命通知9月份下达,要求10月1号报到,先生拖到10月底才去上任。为此。被李正副院长狠批了一通。
就这样,硬着头皮上任的平日里温文尔雅的先生,率先抓了全系的团结问题。对三方面来的人员,尽量做到一碗水端平。先生用自己多年教学的水准、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现场实践经验,加上做人的真实和厚道,使得“各路人马”摈弃矛盾,很快地融入教学工作中,顺利地完成教学科研和现场实习等任务。
在系主任工作岗位上,先生一直工作到1990年。
这年,北京动力经济学院成立,先生原来讲授的水利工程方面的专业课程都取消了,只好改教管理方面的课程。先生自学了运筹学、管理学等,先后开设了水电工程管理、水电工程概论、工程项目质量管理、工程项目管理运筹学、土力学地基基础等课程。先生细数了自己教过的这些课程,大都是他在大学里从未学过的。先生最反对的论调是:那个时代的读书人,都是有钱人。先生认可的说法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读书人是有钱人,而不是全部。
先生的父亲很小时,祖父就去世了。祖母是独生女,她的父亲是私塾先生。为了养家,祖母应聘到北平女子师范学校,教授语文和绘画两门课程,并把父亲供养到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的父亲来到南京工作,全家也搬到了南京。
抗战时,六岁的先生和哥哥、妹妹跟随父母从南京逃到桂林、长沙、贵阳、重庆。一路颠沛流离,住过草房,也住过城墙边用竹篱笆糊上泥巴的房子,还在乡间和村童们一起爬山下河。先生亲历过日本人在桂林的狂轰乱炸,整个城市被炸掉了2//3,一片狼藉。在战区学生进修班读初中时,生活很艰苦,经常赤脚,先生还学会了打草鞋。抗战胜利后,父亲回到南京,不久又到柳州、云南。到处找不到合适工作的父亲,直到解放后,才应聘到北京铁道部工作。
1949年底,先生转学到云南昆明私立五华中学(公立不招生),读高三下学期。辗转奔波的生活,耽搁了高中的代数、化学、解析几何等课程。于是,先生上课认真听讲,学好老师所讲的各门课程。课余,抓紧一切时间补习高中的代数、化学、解析几何,赶上了学习进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1950年高考,先生考了云南省第2名,土木系第1名。
先生很自信自己的教课。一是搞了多年,二是下了功夫。年轻时,记忆力也相当好,一本书全烂熟于心,不带讲稿,就能把220学时上、下册的《水工建筑物》课程讲完。
不知道地道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职业形象?
大概学养、修养达到陈寅恪、沈从文、钱钟书、巴金这些让我们只能仰视的大师们,就到了顶端。身边的一些知识分子,因为时代的痕迹、教育的断层,只是学到了如何生存的技能而已。他们不再儒雅、斯文,已经模糊了这类本应是社会阶层中很优雅、清高的人物形象。尤为甚者,在校园里,或与学生在办公楼前谈话时;或身着笔挺鲜亮的服装走在教室的走廊上,竟毫无顾忌地随地吐痰。笔者亲眼所见时,心中一片悲凉……这,与引车卖浆、贩夫走卒之辈有什么两样?
这些天,我在读北大王风选编的“汪曾祺集”小说集《受戒》。王风对汪先生的评价,很多都是我在整理采访先生笔记时的感受。我是在断断续续读完书后,才看到王风的跋,而我早早就为先生敲定了“雅赏”的基调。在今天喧嚣的尘世间,碰到这样一个清雅、淡泊,仍洒脱生活如先生的人,还真是不容易。
汪曾祺先生的游记、散文,我一直很喜欢读。老先生对吃的品味和文化的理解,也绝不在《舌尖上的中国》之下。汪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被闻一多骂过。后在张家口把个右派当得悠闲自得,画画各类土豆图谱,再或煮或烤着吃。王风评价汪先生:读书随性,写作随缘,从没有规划。作品毫无做作,没有任何拘束。即便是犯忌的题材,也写得落落大方,从而造就了作品的落拓不羁、清雅绝俗。
顾慰慈先生,无论谈起值得自豪的教学工作、风生水起的工程设计,还是做了七年的系主任,语调一直那么平和。即便生活得窘促,依然坦然面对。非常符合这种典型的“清雅绝俗”的人物形象。雅:是与先生接触后的感受。清:则是目前先生生活状况最直观的写照。
先生,让许久隐含在记忆深处的人物形象鲜活起来。从先生的装扮到谈吐,一下子能让人找到那种亲切久违的感觉。想想,过去我们动力系的教授沈自均先生、何适生先生等,那一代人,都是具有这样典型的知识渊博、品行高雅还不乏幽默的知识分子风范。真的很想念他们。
什么样的底蕴?能让这样陈旧的服饰,装点出如此精彩的人物形象?
什么样的涵养?能将人生的岁月、逼仄的境遇,洗礼出超脱、夺目的光泽?
出生在无锡的先生,不仅具备了江南才子的典雅,同时蕴含着坚韧的个性。他的观点也简单:“穿什么无所谓,只要干净就可以。”目前收入6000元左右的先生,每月要交3000元的房租,每天吃两顿饭。但订着牛奶、订阅着《北京青年报》、《京报》和《法制晚报》。所谓历经三代的贵族,就是这样在不经意间,处处流露出品位的雅致和精致。这不需要靠豪车和别墅铺垫,也无法靠几千元的皮带修饰门面。
走出先生的居所。我感受到,京城繁华的街头反衬着先生的俭朴。橱窗里琳琅满目的奢华让人炫目,脑海中先生简单的家,却怎么也挥之不去。一个大学教授、一位享受着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的先生,晚年竟会生活得如此简单。问他今后的打算,依是那样的平静:“已经将自己编的一套书捐给图书馆了。准备再将剩下的还有用的书也捐了,就没什么遗憾了。”
我要找到公交站台,先生说小路太乱,执意要送我。
还是那样的步伐、还是那样的气韵。
看着先生微笑地挺立在寒风中,我眼前幻化出一幅色彩浓郁的油画:恍若看到一位高雅的绅士,正走出金碧辉煌的音乐大厅,或是挂满古典油画的高大城堡,披一身晚霞的余晖,向着清澈河流边的密林深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