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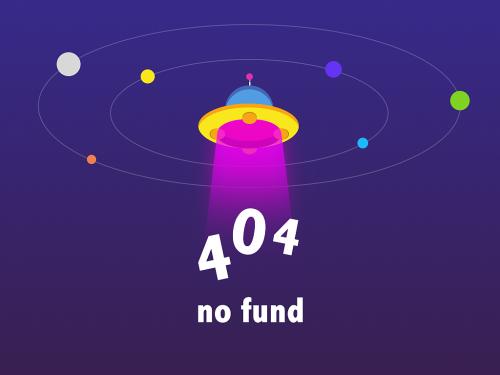
总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般贮存着好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便浮现街衢,显出屋檐,传来蝉语,甚至感觉到不远处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的生之潮流。
收拾行李归家,发现长兴已大变模样。熟悉的街道不再熟悉,陌生的店面林立;最爱吃的那家生煎店已搬迁;母校的校服也换了式样……母亲生我时稍晚,故仗着自己年幼在几位叔叔伯伯家闹翻了天。偏我还长着一副乖宝宝模样,在犯错时一脸卖乖讨好,让家人又气又爱。一次在大伯家和哥哥姐姐捉迷藏,我脱了鞋子进了他家米缸,一躲便是大半个时辰。现下想想,自己也不觉好笑,小时候的皮猴子是如何成长到现在的。
虽没有久客它乡、满鬓白发地归来,但那种近乡情怯的激动与伤感却是小时背过“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我无法体会与领悟的。从被人疼爱到疼爱幼辈,转变只在短短几载。一路迤逦行来,时间是怎样爬过皮肤,只有自己知道。
虽然,那些个遥远的回忆已滑向遥远的地方,带着斑斓色彩的欣喜和五味杂陈的复杂,但生我养我的那个地方永远是我心中最为温暖的回忆。